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的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德国)荷尔德林《人,诗意的栖居》
在中国艺术的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当代艺术如此亢奋的创新冲动,纪连彬就是当代艺术家中突出的一位画家,他的人物画不仅个人风格鲜明,让观者过目不忘,而且探索出了一种新图式——圣像式祥云人物。
纪连彬也是一位风格多样的画家,反应了他在艺术语言上的多向探索。纪连彬的人物画大体上可以分为有“域外印象”、“祥云系列”、“雪域高原”和“梦海系列”。圣像式祥云人物图式指的就是纪连彬的“祥云系列”,也是他在语言探索中属意颇多的领域。起初,很多行内人并不认同“祥云系列”,更喜欢小清新的“域外印象”。原因很简单,“祥云系列”圣像式的构图、浓烈的色彩,逸出了人们的审美范围。不过,对于一个新的艺术语言,或者一种新的绘画图式,现代人已经不再轻易妄自置喙,因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单凭个人立场和纯粹经验的臆断,往往不是历史的观照。法国的印象派与官方沙龙之争、惠斯勒与拉斯金的官司,就是不太久远的例子。艺术本来就是个人行为,艺术家有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世界的权力,或许这就是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分野。事实上,印象派成为西方艺术的经典,再后来,谁能说“祥云系列”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诸子百家”之一呢?
原因很简单,“祥云系列”不仅仅是图式创新,其内涵也是很丰富的。一个仰望天空的画家,有一个观照宇宙的情怀,悲悯人生的肝肠。
不凡的藏族题材
2009年1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灵感高原——中国美术作品展览”,这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藏族题材的美术展览,梳理和汇集了六十多年以来,藏族题材的各个时期的经典美术作品,囊括了油画、中国画、版画、雕塑、连环画、水粉、水彩等绘画形式。
从展览的作品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属于艺术记录阶段,画家没有预设主题,只是记录民族风情,把看到的藏区风采作为创作的内容。如孙宗慰的《蒙藏生活图之歌舞》(1941,中国画)、《蒙藏生活图之集市》(1941,中国画)、吴作人的《甘孜雪山》(1944,油画)、《雅砻江上的牛皮筏》(1944年,水彩),吴作人的《藏女负水》(1946,油画),叶浅予的《甘南速写》(1944)、韩乐然的《拉卜楞寺前歌舞》(1945,油画);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上世纪80年代,以主题为先,语言开拓的阶段。藏族民主改革、民族团结的时事主题鲜明 。如牛文、李少言的《当和平解放西藏的喜讯传到康藏高原的时候》(版画,1952年),石鲁的《古长城下》(中国画,1954年),黄胄的《帐篷小学》(中国画,1954年),董希文的《春到西藏》(油画,1955年),刘勃舒的《牦牛运输队》(中国画,1957年),于月川《翻身奴隶的儿女》(中国画,1962年),朱理存、杨肖丽的《叔叔喝水》(1973年),丹增、光绍天的《鱼水情深》(中国画,1974)
第三个阶段,主题深化为对神性、自然和人性的观照,艺术语言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度探索。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油画,1980年)、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中国画,1988-1998年)、方增先的《母亲》(中国画,1989年)、刘大为的《雪线》(中国画,2004年) 、徐匡《天鹅又回来了》等。这一阶段的藏族题材绘画,没有预设的主题,正如版画家徐匡所言:“作品的主题,不必特别指出”。艺术家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对神、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上,放在了个性化语言的突破上。这时,题材只是作为语言的媒介而存在。
在这次藏族题材的展览中,纪连彬的《云中》(中国画,2009年)参加了展览。一个藏族妇女占据画面的中央,白云缠绕,蓝天映衬,显然,神、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是纪连彬要表达的主题,藏民族的基本元素尽在其中,只是纪连彬将这些元素放大,让观者想起了西方基督教教堂的圣像画。
从《云中》中可以看出,纪连彬是比较典型的第三代藏族题材画家。在纪连彬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幅幅优秀的藏族主题杰作诞生,形成一座座的雪山,挡住了纪连彬的去路。因而,只有一条路——开辟九死一生的“驼峰航线”,这就是他探索的圣像式图式,也就是他的“祥云系列”。《云中》是纪连彬“祥云系列”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幅作品里,艺术家的主要用心放在了语言的探索上。至于主题,与其说没有主题,不如说是关乎神性和人性的形而上学主题。
新中国的艺术家们偏爱黄土高原、江南水乡、戈壁大漠、塞外草原、民族风情,是艺术审美标新立异的特性使然。而对西藏题材,艺术家们更是情有独钟。藏族主题特有的魔力和灵感的元动力,蕴藏在藏族地区独特的异域风情、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可以升华艺术主题,生发各种不同的艺术语言,对新中国人物画的推进功莫大焉。
前往藏族地区写生,并以藏民题材创作的艺术家确实很多。早在抗战时期,就有画家前往藏族地区写生。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当地政府也组织了很多内地画家前往西藏写生创作。老前辈走过的艺术之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但是我们必须在前辈走过的路上继续前行,艺术才有生机。如果重蹈前人故辙,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艺术的特性使然,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大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追求至美是优秀艺术家的天性。
从?年起,纪连彬多次去西藏写生,这里的天,这里的地,这里的人,让纪连彬流连忘返。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彩,西藏黄教神秘的仪式,唐卡,藏民通往精神家园的叩伏,当他仰望天空时,似乎看到了人类灵魂回归家园的欢愉和惬意。此时的纪连彬,眼前出现了上古鼎彝盘曲的云雷纹,传说中盛世的五色祥云。纪连彬此时此刻得到了灵感:何不将可以入画的云的角色放大,与人物一起,成为绘画的主体?这是一个新颖的想法,一个不凡的西藏题材。首先,纪连彬跳出了几十年来,中国现代美术对西藏题材的认知,回归以中国诗学的赋比兴为思维方式的文化机制,来表达人与神的交流,导引观者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思考。
图像的力量
“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这是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中的开篇,阐述汉字的缘起。中国古代的圣贤仰观俯察,其目的是寻找自然的法则,并以卦象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以遗后人。后世希圣,代代不乏仰观俯察者,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脊梁。
书画同源,中国绘画何尝不是如此呢?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引颜延之的话说:“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张彦远认为,绘画与卦象和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可以“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佛教称佛教绘画为“象教”,我们现代人叫做图像的力量。
细品纪连彬的“祥云系列”,人物列于五彩云霞之中,人在升腾,云在飘逸;题材是藏族题材,人物是藏民,唐卡的色彩,西藏洁净的蓝天白云,其寓意很明确:精神的升华、生命的庄严、灵魂的净化。
中国艺术善于运用形象来表达观念,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形象表达文化观念有一种成熟的机制,这就是赋比兴。《诗经•关雎》一诗,以鸠鸟来比兴男女爱慕相守;屈原《离骚》用香草美人来比喻忠臣贤士;东晋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以菊花寄托箪食瓢饮的清高气节;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诗以“野渡无人舟自横”来比况自己满腹经纶而无人提携;唐伯虎用“秋风纨扇”来抒发美人迟暮、英雄落魄的感伤。试想一下,以《富贵》、《忠贞》为命题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赋比兴的文化机制,这些抽象的观念是很难用形象来表达的。中国画家画出生动可喜的牡丹花,就是富贵的意象,苍劲的松柏就是“岁寒而后凋”的忠贞意象。中国画家甚至可以画出声音,老舍曾经给齐白石出了一个画题:“十里蛙声出山泉”,齐白石画的是蝌蚪从山泉中游出,观者看见灵动的小蝌蚪,自然会联想到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词句。
假如一个画家要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神性这样的观念,也都是用形象。在这一方面,中西方使用的形象有所不同,西方艺术中运用的是光,寓意神无上的智慧。比如基督教绘画中耶稣和圣徒头上的光环,贝尔尼尼的雕塑《圣德蕾莎的痴迷》的顶光,佛像中的光环等。中国人用五色祥云象征神赐的祥瑞,故中国艺术中经常使用云的形象,比如中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云纹,中国的山水画中也经常出现云,以此来表现阴阳调和的意向。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的神。唐代诗人杜牧的《云》诗:“东西那有碍,出处岂虚心。晓入洞庭阔,暮归巫峡深。渡江随鸟影,拥树隔猿吟。莫隐高唐去,枯苗待作霖。”云千形万态却虚无缥缈,变化万方而无心无意,高高在上可沛然作雨,这正是云的神性。中国东晋著名的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公正是以闲云自况,分有云的神性。
纪连彬的五色祥云兼有神性和吉祥的双重意象,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气氛里,白云是神的昭示,是洁净的、吉祥的象征。纪连彬将洁白的云观念化为五彩的祥云,一是出于艺术语言的需要,二是汉文化中五行转化为五色的色彩观。
色彩的宇宙
纪连彬的用色十分讲究,他用明快的黄色、藏蓝色、白色和红色——藏族地区特有色彩。纪连彬借用了藏族人民的民族色彩,观念确实汉民族代表五行的五色观。我们知道,中国绘画的色彩是观念色,西方绘画的色彩是固有色叠加环境色。中国绘画的色彩是画家所在的文化共识的内在色彩,而西方绘画的色彩是物象的外在色彩,只有在印象派以后的绘画中,画家才大量使用个人的(非共识的)主观色彩。这是两大文化体系绘画色彩观的基本分野。
我们的先民具有自足的宇宙观念,即阴阳和五行的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的繁复驳杂,无外乎阴和阳。《尚书•洪范》中提出了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作用,用宋代王安石的话说:“天所以命万物者也。”宇宙万物勃发,只不过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当然是形而上意义上的元素)。对应于五行的是五色、五味、五脏、五德、五个方位等,因此五色青、黄、赤、白、黑是自足五行宇宙的色彩表达方式。中国人看见的五色不仅仅是颜色,还有更多的意义包含其中,这时的五色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宇宙的圆满和浃恰。比如《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孙星衍疏:“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出於黑,故六者有黄无玄为五也。”对应于人事,五色象征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的是人生的幸福和圆满。可见,汉民族艺术以五行的色彩观念作为色彩语言,汉藏两个民族的色彩观念在这里殊途同归。
物象的升华
纪连彬的创作之路是典型的当代中国一线画家走过的路,毕业于美术学院,受过严格的造型训练。早在十几年之前,范曾先生看到纪连彬的人物画作品后评价说,这位画家画得好。一位业内自视甚高,极少称许同行的先生,对纪连彬有这样的定位,是对纪连彬绘画素养和艺术天赋的肯定和期许。然而,纪连彬也是一位后脑勺上长有反骨的画家,学生时代的纪连彬就经常冒出一些不合学院规范的想法,经常画一些老师不喜欢的作品,这让年轻的纪连彬很苦恼。时任纪连彬任课老师的许勇先生慧眼识珠,称赞纪连彬敢于创新的艺术精神,鼓励他继续探索,使得纪连彬对自己的艺术观念有了一些自信,坚定了走自己艺术道路的决心。在长期孤独的艺术探索中,反叛转化为艺术的自省和升华。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的中国,是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多艺术人才的国家。新的时代,新的艺术观念,催生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然而,中国画却“有高原没有高峰”,时代呼唤仰望星空的艺术家。究其原因,是艺术家自身创造力的缺乏,还是艺术土壤的贫瘠,这是各方有待商榷的课题。在艺术的丛林里,有人迷失了方向,消失在纷纭的艺术观念之中。但总是有人走出来的,纪连彬就是走出来的艺术家之一,这得益于他的某种不甘平庸的性格,得益于他不随波逐流的艺术叛逆和东北人的倔强。可以说,从驾轻就熟的物象描写到形上的观念表达,这是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巨大的跨越,其风险是两头不靠,跌入深渊。艺术家的人生没有几个十年,敢拿自己十年的生命作为赌注,押在师友们并不认同的艺术样式——“祥云系列”上,没有一种坚定信念是做不到的。
灵魂的家园
有一位评论家说,纪连彬的“祥云系列”是有想法的。意思是说,纪连彬不仅仅在创造一个新的图式,更重要的是,图式的背后试图营造一个灵魂的家园。
提出了人类灵魂家园建构的命题。在人类追寻灵魂的安顿之所的时候,宗教提供了一个彼岸的、来世的家园,而艺术提供了一个此岸的、现世的家园。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以艺术代替宗教,意在以一个现世的精神家园代替来世的欢愉天堂。纪连彬的“祥云系列”,不是现世世界的摹拟,也不是宗教教义的图释,画家试图将宗教和艺术的家园合二为一,构建一个此岸与彼岸的桥梁,人与神的通衢,灵魂与肉体的走廊,宗教与艺术的航线。在圣像式的构图中,高高在上的不是神,而是平凡的藏民。因为这样的构成,观者也无法将他们视作普通的藏民,而是具有洁净灵魂的人物,圣徒式的人物。人物头上的五彩祥云,那是神赐的祥瑞,是人类精神的欢愉。在这里,人与神的世界得以沟通,人的精神和神的意志得以统一。在这种人与神的通感中,写实的艺术得到了升华,升华为宗教的冥想,升华为人生的自省。
下一篇::一雁南飞 成就苏武
- 潘天寿的中国画思想
- “中国国家画院2018访问学者、高级研修班”结业作品展暨结业仪式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
- 异变——蒋佑胜个展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开幕
- 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复评评审会在京圆满举办
- 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复评评审会在中国国家画院举行本届展览首次新闻发布会
- 著名艺术家梅墨生逝世 享年60岁
我有话说
最新文章
- 1潘天寿的中国画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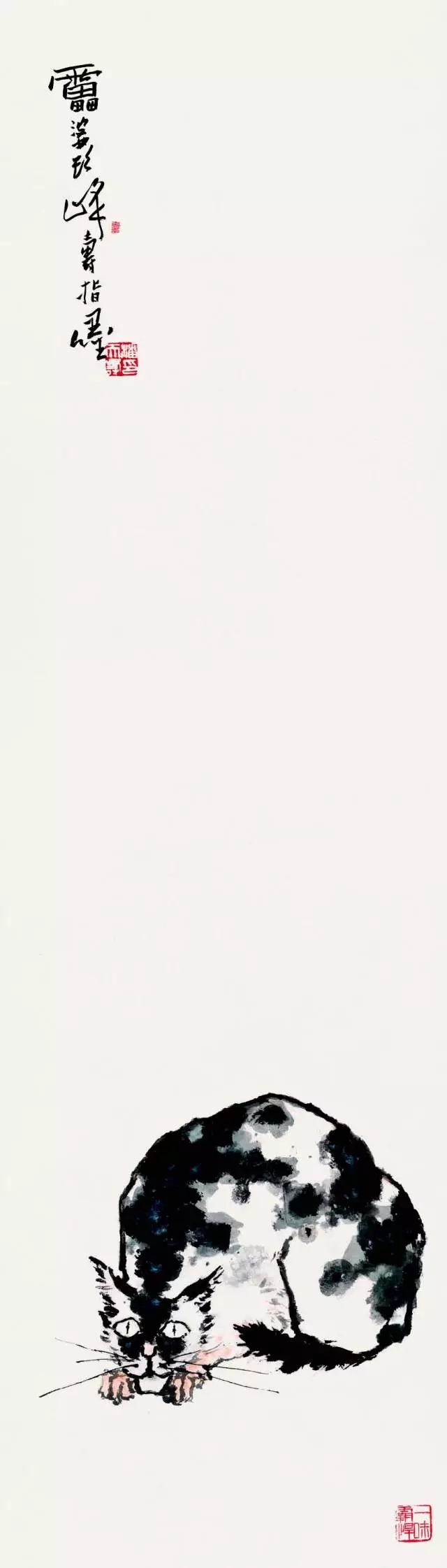
在现代中国,面临西洋画的冲击,中国画大有式......
- 2“中国国家画院2018访问学者

2019年7月2日,“中国国家画院2018访问学者、......
- 3异变——蒋佑胜个展在西安崔

2019年6月22日,“‘2019猎质·历史的个体症状......
- 4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复

2019年6月20日,“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
- 5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

6月21日下午,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复......
推荐文章
热门文章
- 1中国古琴美学展登陆上海 传统艺术

“乘物游心——中国古琴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
- 2第五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作

7月26日,演员在表演舞蹈《天边那片绿云彩》...
- 3袖中雅物:与团扇的不解之缘

扇子种类比较多。晚明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
- 4潘天寿:书法之本乃精神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县人,现代著名画...
- 5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

三阳开泰轴明代朱瞻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