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是一面镜子,即照着自己也映着别人。李乃宙在人物画领域探索了近30年,具象写实是他长期以来追求的主要形式语言,他的题材较多是表现矿工和山村的普通劳动者,其画纯朴自然、平淡天真,人物造型功底坚实,其笔法不虚语,墨法不混沌,密中求实,秀润华滋,充满了真率、单纯、朴素、明朗之美。
李乃宙先生的艺术才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山水、人物、花鸟皆能。但是就其个人来说,他显然更热衷于人物画创作,成就突出。
乃宙先生对于人物画的情有独钟,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和个性有关。他曾经回忆过一段童年往事:上小学时有一位姓罗的先生热心教他临摹芥子园山水,天天学画披麻皴,但是不多一会儿,就罢课了。—“后来我还是觉得自己更喜欢画人”,他说。为什么更喜欢画人?回答得很直白:“与人的对话比与山水的对话来得更直白一些”。(李乃宙《人生在途》)“直白一些”,可谓一语道破了乃宙先生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上之所以专注于人物画创作的玄机。事实上,这种“直白”的观念确乎是一直影响着乃宙先生的绘画风格的。他的人物画始终充满了“直白”的真率、朴素、单纯、明朗之美,就跟白乐天的诗一样。乃宙先生可称为当今画家群体中的白居易,他的很多作品都充满了风俗画的意味。在袅袅蓑蓑、怩怩歪歪的艺术风气弥漫画坛的日子,乃宙先生的作品就是以不事雕饰,自自然然,坦坦率率的美学品格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任何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或精神内核,都必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表现形式,才能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这于乃宙先生来说,也不例外。他崇尚“直白”的美,那么就必须掌握一种最能直接、准确地捕捉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他要把这种美“直白”地呈献给读者,就必须建立一道便于读者与艺术家之间进行自由沟通的桥梁。
于是,在存在于现代中国画里的抽象变形与具象写实这两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之间,乃宙先生便选择了后者—“具象写实”。
他藉以这样的一种绘画方式从看似寻常的表现形式上显示了最大的奇崛。
不过乃宙先生发觉,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选择。更多的人喜欢“变形”,玩“怪异”。
曾有人说作家汪曾祺的文字拆开看一个个都平平常常,“寡”得很,黏成句子就趣味横生。现在很多人对于“具象写实”也看不起,认为“寡得很”,是笨人干的活儿。对此,乃宙先生又拿出了他一贯的“直白”:
“绘画之道,在于表现。抽象与写实的表现都源于画家的认识……如果你是很怪异的性格,那么在作品中一定会表现出那种不可思议的方面来;如果你是一个纤弱、多愁善感、感情丰富的人,那么你的作品一定就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方面的因素。……(我)认识到自己不具备‘怪异’的灵感,又不具备追求时髦的气质,只能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地做学问。”(李乃宙《砚边拾遗》)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不过我不相信他不会玩“怪异”。但我相信他能玩一时,不能玩一世他怎么能玩一世呢?他根本就“不具备‘怪异’的灵感,又不具备追求时髦的气质”,结果,只能“老老实实、循规蹈矩”地待着。但是,他做出了“学问”。他的人生和他的艺术一道:不“寡”!
早在1973年,乃宙先生即以人物画力作《矿党委书记》参加了全国的连环画中国画美术作品展览,登上画坛。《矿党委书记》运用的就是一整套写实技法—写人物肖像之实,生活场景之实,内心思想之实;以“实”突出了一个奋斗在第一线的矿党委书记的形象,并以“实”使笔下的人物与陌生读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共鸣。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实”力……进入80年代之后,社会发生了巨变,乃宙先生的艺术生涯也随即跨入一个新的里程。从1982年至1984年,短暂的两年时间,对于乃宙先生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1982年,乃宙先生以一位业余画家的身份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卢沉、周思聪先生。在两位名师的悉心教诲下,他得以对以往的绘画思想和表现形式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理论和实践都有质的飞跃。对于两年的学院教育给自己的人物画创作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启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
“人物写生我一直以写实的方法处理,变形手法会使人物变得夸张,对于变形夸张我始终不得要领,变得太丑不对我的‘胃口’,如果不变又觉得‘味道不足’,在两难中我得找一条折中的路。卢沉、周思聪先生不同的表现方式让我茅塞顿开,卢先生写生不用碳条起稿,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准确,个性鲜明;周先生造型用笔朴拙但人物形象却夸张生动。我感到了艺术的震撼力,领略了艺术的真谛。两年的学院教育,使我充实了很多,大量的人物习作和人物速写为随后的创作做了铺垫,创作思维符合艺术规律,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李乃宙《人生在途》)
透过两位大家个性鲜明的画面,艺术嗅觉灵敏的乃宙先生似乎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笔下的“味道不足”,他想“变”。但他又不想“变得太丑”。他陷入了“两难”。他迫切地需要找到“一条折中的路”。于是,在两年后的毕业创作中,他推出了《小字辈》。
小字辈依然是人们熟悉的人物,“年轻的矿工”,“新一代开拓者”,漂浮着乃宙先生曾经工作过的抚顺煤矿的记忆。谁都认识他,他就在我们的身边,“熟透了”。不熟的是小字辈身上的线条,那大块面的墨色,跟矿党委书记完全不一样的着装,有劲头。小字辈身上散发着一股新鲜气味,就像他身后那一圈圈的线缆,一根有一根的精神……小字辈依然是“具象”的。小字辈的眼睛还是黑得很透明,看得见长了翅膀的心灵。只是“直白”得更文雅一些,也更潇洒一些。《小字辈》—就像乃宙先生自己说的—“创作思维符合艺术规律,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小字辈》登上了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领奖台,成为乃宙先生在主题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由《矿党委书记》到《小字辈》,人们领略了乃宙先生运用写实手法创作重大题材的过人才华,也通过一幅幅生动的“具象”明确地感受到“直白”意识的独特魅力,乃宙先生的足迹是稳健而清晰的。
1989年,乃宙先生以《晚秋的柿叶》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跟《小字辈》比较,《晚秋的柿叶》又变了—从表现手法到艺术情境。这是乃宙先生创作生涯中一件闪烁着别趣的作品。他以一种非常轻松,含蓄,近于诗意的笔调展示了发展中的国家新一代乡村少女的形象。乃宙先生曾经在四川攀枝花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他应当熟悉攀枝花的一支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民歌里的人物场景和《晚秋的柿叶》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民歌是出现在晚清,而《晚秋的柿叶》则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出现在我们日子里的作品。心思不一样。《晚秋的柿叶》里的少女在想什么呢?“对山梁般宽厚的男人肩胸,不再觉得充实,虽是山里的妮子……她却以新奇的眼光眺望,要去更远的山外,重铸少女心中的憧憬,走出去—领略全新的世界!”乃宙先生借别人的话(诗)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站在晚秋的柿叶里的少女,心里已经发了一枝柳芽,像她那一小卷儿围巾的颜色。晚秋的柿叶里的少女,是一个群体真实的缩影,代表了一个季节(时期)的人的心意。乃宙先生以诗的笔调写成了《晚秋的柿叶》。
进入90年代以后,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乃宙先生突然从我们的日子里走出去了。走得很远。走到了杜甫、王维、白居易、皮日休的意境里。后来,他又回到李叔同生活的时代。他是不是腻烦了他笔下的那些熟悉的气味,那些声音?不好说。他可能是想放松一下自己,就像到什么园林的遗址里去遛个弯儿;他也可能是刻意地“收收”自己,让笔下的每一根线都蕴藉一些、雅气一些。也可能都不是。
但是李乃宙就是李乃宙。他还是那么“直白”。他的艺术思维早就踏上了一部结实的三轮,在今天的胡同里悠来悠去。
近年来,乃宙先生的人物画创作已进入了一个优游从容的境地,有一些“化”的征兆。让我看了特别震动的是创作于2003年的《民间艺人》。民间艺人的形象—特别是面部,尽管仍旧是“具象”的(就跟当年的矿党委书记一样),“实”得几乎让人听得到艺人的某一根银须在轻微地抖动的声音。但是塑造艺人的手段就如同画里的艺人一样,已经达到一种很“老”的境界。人物衣纹的用笔,无心峥嵘,只顾平淡,随便一勾,毫不费劲。而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是艺人的神情。—除了生活中,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从别的什么地方碰到过这种神情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我没听说乃宙先生以前曾结交过卖唱的朋友,没遮拦地说过知心话,想象不出他会从什么地方忽然捉住了这么一把神情,只能相信他在画中说的一句话:“中国画虽是表现性艺术,写实仍是表现的一种方式”—“要有扎实的造型能力”。是的,我猜测他可能是收集了很多天桥下、胡同里陌生的艺人实实在在的形象,然后,把他们扎实地“写实”下来了。
乃宙先生很多很有力度的作品,的确就是“写实”的。写得很扎实。生活中很多很新鲜、很独特、很有意味的东西,我们不暇(或以为不屑)注意,乃宙先生都一门心思地把它记录了下来,等见到了他的作品,眼睛全亮了,又惊喜又嫉妒。
他曾经画过一张《曹无》(1999年作)。我不认识曹无,看着他身后几枝折了的莲蓬(一个花骨朵都没有),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就胡思乱想,想得很忧郁。后来,我打电话给乃宙先生,电话那头传来这么一串声音:“没有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就是在我的画室里画的曹无,当时他站的地方刚好有这么一堆枯荷,我就把它画下来了。” 看来,是我自己的心田支满莲蓬了。
我还见到过他一张《退休者》(1999年作)。退休者端端正正坐在那儿干吗,旁边还搁了一只鸟笼?他不干吗,他就在那儿待会儿。“民亦劳止,迄汔小休”,他忙活了一辈子,需要休息,小坐一会儿,脑子里空空的,“松快松快”。他不是诗人、哲学家,也不是退下来的国家干部,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喜欢那么什么也不想地待着,谁也管不着。
面对一张画,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好思索”的欣赏习惯。很多人都养成了这种欣赏习惯。乃宙先生的笔可以治一下我们的这个通病,把它纠正过来,大家都轻松。
一系列以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是乃宙先生近年创作中的另外一个核心。画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不能完全依赖题材。这种作品已经很多(以前多是工笔,现在也有一些写意的了)。乃宙先生的《苗岭三月》给人的感觉是稀奇的(不惟新鲜)。他借用了类似摄影艺术中的“特写镜头”,不招呼一声就把一个春天的苗人“推”给了眼睛们—噌的一下子不知从哪儿蹦出了那么多,一个顶一个的,白花花一片,全是“银”!“大街小巷一队队身着盛装……硕大的‘牛角’头饰,银光闪闪,直向云天……”(李乃宙《〈苗岭三月〉创作随笔》,以下同)。够意思。
情景是真实的。
乃宙先生曾多次深入苗乡。—沾沾自喜地嗅闻那里的气味,寓目一些优雅的颜色,大口吃凯里的酸汤鱼,一圈一圈地绕在巷子里,突然瞪大眼睛,“冲天的牛角头饰、叮当作响的环佩、婀娜多姿的翩翩少女、明快欢畅的芦笙恋歌,鲜活,秀美,悦耳,流畅,和着温润的阳光……”他被溶了进去,像掉进梦里,醒来,就有了《苗岭三月》。
《苗岭三月》用了咱们自己的—散点透视,沈括式的“面面观”,大家都有脸。走在《苗岭三月》里的苗人,就像《红楼梦》(庚辰本)第十五回说的:“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 张宗子写《西湖七月半》时是这样开头的:“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七月半之人。”苗岭三月,春色里的一叠一叠的峰峦,一个角也看不见,只看见三月里之人。
《苗岭三月》获十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同时得了个十届美展特别奖项—齐白石奖。喔,齐白石,这个曾经说了一句“—吃鸽子蛋,有力气”的伟大的山民艺术家!
乃宙先生以“直白”的观念,用“具象写实”的绘画方式,已经在画坛驰骋了30年。他没有改变他的观念,或者说表现形式,他只是在日益丰富他的观念和表现形式。一步一步,他就这么过来了。如果有人问:乃宙先生为什么要画这样的画?为什么老这样画画?不如说: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乃宙先生天天生活在生活里,一步也不肯离开。
下一篇::张卫:状态
我有话说
最新文章
- 1情满大别山——大别山精神暨

开幕式现场6月15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
- 2卢禹舜•天地大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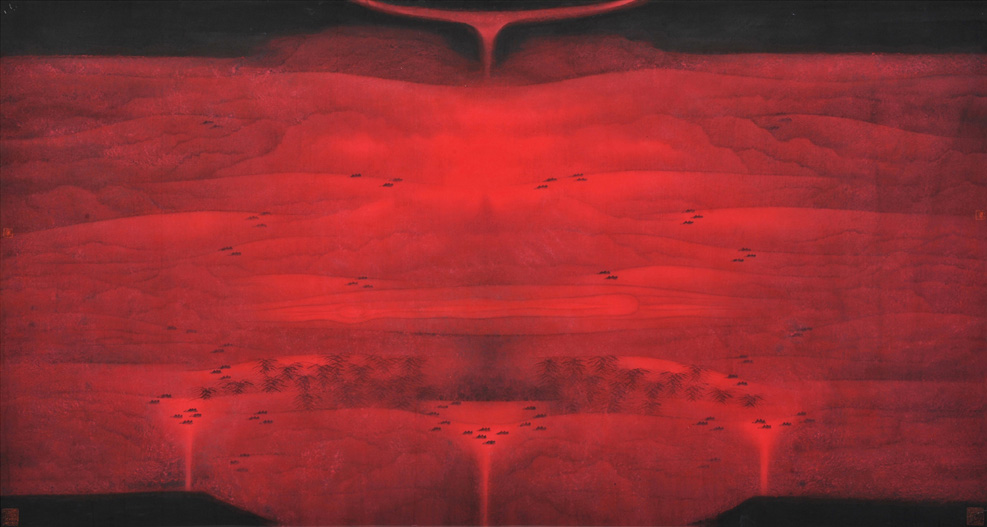
......
- 3张复兴•太行春霁

......
- 4贾广健•碧水金荷

......
- 5富中奇•乡情

......
推荐文章
热门文章
- 1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

三阳开泰轴明代朱瞻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
- 2袖中雅物:与团扇的不解之缘

扇子种类比较多。晚明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
- 3潘天寿:书法之本乃精神

潘天寿(1897-1971),浙江宁海县人,现代著名画...
- 4中国古琴美学展登陆上海 传统艺术

“乘物游心——中国古琴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
- 5第五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作

7月26日,演员在表演舞蹈《天边那片绿云彩》...